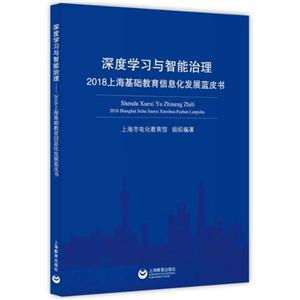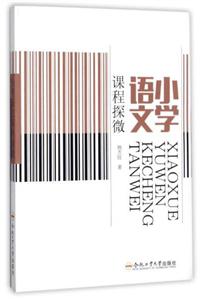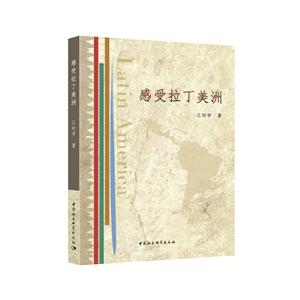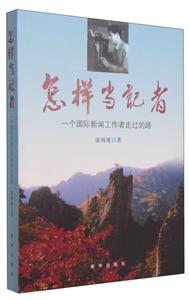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
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作者:汪介之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5334-6374-8 定价:68.00 元 出版时间:2015-01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第一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等等,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中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第一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第一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下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否能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是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等等……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的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重版后记 (节选)
汪介之
复旦大学杨乃乔先生主持编辑一套“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嘱笔者从已出版的著作中挑出一本,作为这套文库的一种。忝为被选中的文库作者之一,我自知个人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不宽,成果有限,现只能不揣浅陋,谨拣出这本前辈学者尚较为认可、同行朋友常有提及、同学们也较爱看的《远逝的光华》,稍做文字上的修订,呈送乃乔先生及福建教育出版社董伯韬先生、李杨先生等审阅,以感谢诸位先生的厚爱,并表达对这套文库其余各位著者的敬意。
比较文学研究应当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而笔者却仅仅侧重于中俄文学关系这一领域,这并非我自觉选择、自我限制的结果,种种因素早在我能够做出这一选择之前,事实上就已对它进行了框定。我学习的外语语种为俄语,专业是俄罗斯文学,毕业之后所从事的研究,很大一部分仍然属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每当我阅读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考察一位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或注目于一种俄罗斯文学现象时,都不能不想到它在我国的解读与接受,同它的本来面貌、同它在俄罗斯本国批评界及本国文学史著述中的评价之间有何差异,不能不想到它对中国文学是否产生过影响或产生过何种影响,进而追问造成这些差异与影响的原因。同时,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同样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历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著述与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哲学、艺术乃至宗教与伦理思想的广泛渗透。俄罗斯知识界在研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程中,也建构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显示出富有特色的俄罗斯式的解读。这些解读不仅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史册,而且能以其特有的“旁观者清”的视角,启迪我们进一步认识自身的文学与文化。笔者的上述阅读与思考心得,先后凝结为若干篇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和几本拙著,后者主要有《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合著)一书。
除此而外,我的其余研究,大都似应被看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也即外国国别文学研究。不过我也常常想到,我们中国人所做的任何外国文学研究,其实都显示出一种中国立场,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眼光,因此也就完全不同于外国学者对本国文学的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包含“阐发研究”,也即以一种外来理论模式解释本民族的文学现象,那么,从中国文化—文学的立场与视角去阐释外国文学,自然也应当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丹纳(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建构,当然不同于英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任何一种《英国文学史》。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大著《19世纪文学主流》关于法、英、德等国文学的描述与评论,当然也不同于这三个国家的学者对本国文学的评价。作为一名丹麦学者,勃兰兑斯在谈及自己为什么“放下”丹麦文学而去研究西欧文学时曾经写道:“整个说来,我间或偶然地提到丹麦文学。……这倒不是我忘却了或者忽略了丹麦文学。相反,它一直在我的心中。既然我试图陈述外国文学的内在历史,我就在每一点上都对丹麦文学做出了间接的贡献。我将画出必要的背景,以便我国的文学有朝一日能带着自己的特征在这上面显现出来。……如果这个方法是个间接的方法,那么它也因此是个更坚实的方法。”不言而喻,勃兰兑斯所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其实也是比较文学研究。《19世纪文学主流》无疑既是关于19世纪西欧文学研究的一部经典性的学术专著,又是一部出色的比较文学研究巨著。它不仅雄辩地说明了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必然具有比较文学的意识和视野,而且也告诉我们: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比较文学。正因为如此,目前我国学术界已越来越趋向对以下观点表示认同:中国学者所进行的外国文学研究,其实都是一种比较文学研究。
社科图书 文学艺术
在线阅读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无相关信息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