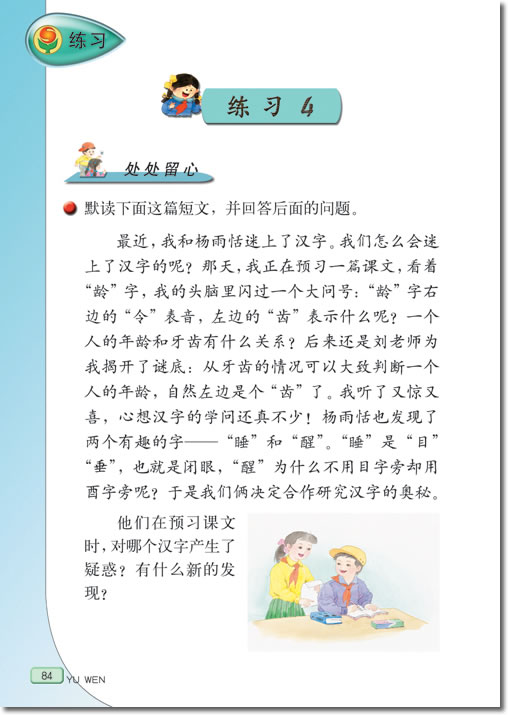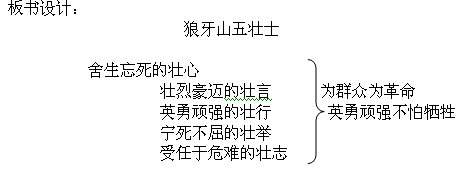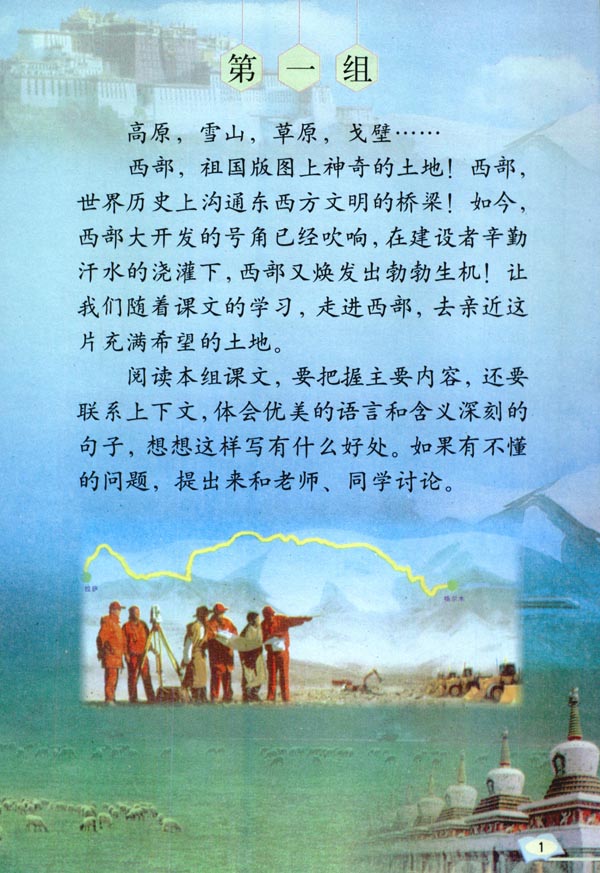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心灵,诗一般的老人
沪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三、老人篇
关于文中老人的外貌描写、语言描写以及动作神态描写,不难发现,均有个共性特点,即她总是“静静的”,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看着“我”,静静地期待着,静静地打着节奏……这与个人的精神气质有一定的关系,如老人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曾经是乐园的首席小提琴手,一个有修养、有内涵的老者。她言谈举止总是波澜不惊,但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很深的,无论是与人交流、看人的眼神、教育人以自信,都给作者甚至我们读者一种安娴而美好的感受,这是人物形象所散发出来的艺术生命力、精神感染力,也正是不华丽不堆砌辞藻的朴素语言、朴实人格所带来的阅读美学享受!如果非要找一些比较生动的,有点诗意的言语的话,那么我想只能是以下三个方面了。
第一个方面,老人的平静的眼神。文章有三处描写老人的眼神,如,“一位极瘦极瘦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木椅上,平静地望着我。”“她一直很平静地望着我。”“她慈祥的眼神平静地望着我,像深深的潭水……”老人一开始静静地坐着,可能并不想打扰“我”独自练习,也可能她住在12号楼,或许对“我”在家里练琴受讽有所耳闻,故想尽可能安静地坐着以免使作者担心害怕,至少这样静静地望着作者是在用默默的眼神鼓励他。而老人一直很平静地望着他,对作者是非常有耐心的,更是相信作者的一种表现,这种无言的鼓励,一直陪伴着作者的点滴进步,老人的默默无言、静静注视,是作者获得坚持拉琴的勇气所在,也是老人坚持不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教育鼓励作者的美好品格的最好见证。老人以诗一般的眼神传达给作者信心,这是一位诗一般的老人!
至于,老人的眼神平静得深深的潭水,这还得从“潭水”这个意象说起。李白曾写《赠汪伦》诗,其中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表达了诗人与汪伦之间深厚的友情,“潭水”也作为友谊、感情深厚的意象代表。“潭水”其实正如一位沉思的哲人。它静默地坐在回忆和展望的坐标点,洞察幽微,观照来去,实现了静和动的完美结合。感受潭水,比如倾听花朵孕育和开放的声音,需要我们用灵魂。感受潭水,是我们感受生命的一种境界。我们不妨从这些意象中断章取义:老人平静的眼神像深深的潭水,是不是老人给予作者的教育之恩、关怀之情如潭水般深厚呢?是不是老人也正如一位哲人,洞察作者不够自信需要鼓励的内心世界呢?如果这样来理解,我想用深深的潭水来理解老人的眼神是比较容易的。不过,教学中要让学生明白这一点,恐怕这样光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老人的外貌描写。关于这点,前文已经提到了一些,这里补充一点:老人虽然身型瘦削,满头银丝,但她给予人的整体感觉是慈祥可亲,面善儒雅,给人一种如沐温暖春风般感觉,难怪一个几乎丧失练琴信心的青年在老人的无言鼓励下找回了信心,而且所演奏的乐曲让专修音乐的妹妹“大吃一惊”,这就是人格的力量,这是老人的诗一般的心灵的外在显现,人格的力量在展现在外在情貌上、展现在一举手一投足之中。
最后说第三个方面——老人的诗一般的语言。文章直接描写老人语言共四句话:“老人叫住了我,‘是我打扰了你吗?小伙子?不过,我每天早晨都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想你一定拉得非常好,可惜我的耳朵聋了。如果不介意我在场,请继续吧。”“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每天早晨?”“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小伙子。”老人的话语虽然从字面上、情感上看来是句句真诚,但从客观事实、理性的角度来觉知的话,这是老人保护作者自尊心、自信心的一种善意的谎言、美丽的谎言!从老人说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出,老人非常的谦虚有礼、态度和气,与前文所描述的作者的家人简直天壤之别。言如其人,老人的语言是她人格魅力的体现,是她美好心灵、诗一般心灵的体现,这样的老人肯定是一位诗一般的老者!
不过,这里更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被老人诗一般的语言打动了”的理解。从我们的常规思维来看的话,那些字句稍微整齐的、有些韵律的、形式如诗的文字形式像诗。而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一书中认为,“诗是最精妙的观感表现于最精妙的语言,诗以文字意义和声音节奏来咏叹情趣。”如果以朱光潜先生对诗的理解来看,那么情趣性是诗的一个基本表现特点。文中,老人无非是说了两句话——“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每天早晨?”无论看形式还是内容均不像学生意识当中的诗的样子,怎么会说是“诗一般的语言”呢?如果我们用文学分析的还原法来理解,按朱先生所说的诗的情趣性来看的话,可能就能容易理解了。当时作者在练琴是不自信的,甚至还是有点自卑的,家人是从来不好好听他练琴,更不要说用心听了,他们无非听了几次就妄下定论,一棍子打死了“我“的美好的练习愿景,对“我”的心灵伤害是非常大的。然而,老人说:“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的。”老人愿意听作者的如锯床腿般的声音,而且是用心感受,这对于我来说是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的,有如喝了蜜一般甜,“我”的心情愉悦起来是可想而知的,尽管是一句平平常常的话,但在我听来是美好的,诗意一般的。因此在作者的心目中是诗一般的语言,而且这语言已经超越了诗!还有,老人说,“我能做你的听众吗,每天早晨?”老人甘愿把自己当作是听众,这这个角度来观照的话,那么“我”至少是一个演奏者,或者说是一个演员,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肯定,“我”心里的感觉肯定是美好的。而且老人愿意每天早晨来做听众,这里通过一个倒装的句式强调“每天早晨”,这对于作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有人愿意来当听众可能说明“我”拉的曲子还不那么差,而且愿意每天来听,更可能说明“我”拉的曲子能够陪伴这位“耳聋”的老人,尽管她“听不见”。作者知道了老人愿意每天来听她拉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在家里“数次”拉了以后就受到嘲讽是完全体会不到的美好内心感受,这种体验是非常美好的,这种当下的情感也是非常美好的!老人这样的语言所带给作者美好的情趣如同诗一般!尽管老人的这句话也普普通通,但它所产生的对于作者心灵的触动是无法用言语形式表达出来的,即使是诗也未必做得到。老人所说的触动了作者的内心深处被掩埋长久的美好感受的语言肯定是诗一般的语言,哪怕在形式不像一首诗!这样的语言,只有心灵如诗一般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语言也只有如诗一般的老人才会有!
有这样一位诗一般心灵的老人在无言地默默鼓励我,我从一个即将走到自卑、绝望的学习悬崖边缘的时候回转过身来,看到了一个诗意的美好世界——只要找回自信、拥有自信,努力练习,肯定能够奏出美丽动听的人生乐章的!后来,拉小提琴成了作者——郑振铎无法割舍的爱好。尽管拉提琴并不是他今后的主业,但这是他无法割舍的、已经融入到他生命当中去的爱好,这是因为文中的老人以诗意般的、美丽的谎言保护了一个小伙子即将丢失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这对于他今后的人生道理可谓是非常重要的。自信指引是人生航道的灯塔,自信是成功的基石。郑振铎之所以成为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就是由于一个老人曾经以无言的鼓励、美丽的谎言让他重塑信心,为此,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论面对成功还是坎坷,他都会不由得想起这位“耳聋”的老人,这位在心目中、生命中唯一的、永远的老人!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上一篇:鲍叔牙真心待友
下一篇:《唯一的听众》综合资料之一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