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教亟须加快教育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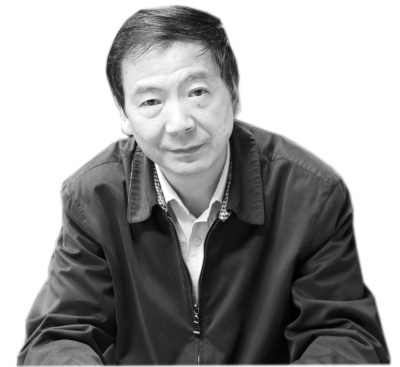
访谈嘉宾
吴恒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访谈嘉宾
朱永新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教育领域里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用立法来解决。要从教育特征出发思考教育立法。
■很多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法律没有强制性,所以才会感到“无法可依”。因而有必要在考虑下一步新增或修订教育法律时,增加强制性作用在教育法律中的进一步体现。
■教育立法不能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而要充分发挥专家和第三方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要注意立法工作中部门倾向的问题。
■本报记者 蔡继乐 李凌 唐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那么,我国当前教育立法工作面临哪些现实问题?教育立法中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教育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恒和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教育立法仅靠“六修五立”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法治体系、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对教育来讲就是要加快教育立法进程,落实依法治教。那么,在教育立法过程中到底如何把握好教育的特征,做到科学立法?
吴恒: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好教育立法则有必要从教育的四个特征出发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教育是现行主要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再次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按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努力和需求总体上还是不相匹配,教育就是这个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即使在农村地区,吃饱穿暖都基本达到了,人们对教育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教育问题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教育总量的问题,而是教育的结构和水平高低的问题。由此来看,我国的教育立法工作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进行,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能说国外有的我们一定要有,也不能说我们有国外没有的就要取消。
第二,教育是个人行为与国家行为的交织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教育是法定的国家行为,也是个体行为。这首先体现在每个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不同,也跟教育的方式有关。说到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必须要靠教师来实施,教师授课时有很多技巧和施教方式,这些都取决于教师个人的素养。对国家行为来讲,法律具有强制性;而对个体来讲,法律就比较宽容。比如个人违反相关规定,义务教育法说“要进行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并没有说给任何处分。这就是说,在教育领域里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用立法来解决,散布在千万家庭里的个人行为,你能用一部法律把它框定吗?
第三,教育是涉及多个领域的多因素的集合体。教育需要投入、教师、手段、场所、环境,等等。因此,我们就要去深度分析这些因素和环节的内在关系,在其中找到起支架作用的关系来立法。这样的教育立法才更有针对性。
第四,教育是意识形态与物质实体充分融合的现实空间。教育属于上层建筑,但学校是实在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把校舍、设施等硬件搞上去了,就说教育做好了。
总体来讲,法律具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法律的规范作用是由指引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预测作用和强制作用五个方面构成的。在这五个作用中,很多人只关注强制作用,这也很容易理解,一讲有什么纠纷,就打官司。这种看法不完整,如果把五个作用都理解清楚,对于教育立法和依法治教的认识才能比较全面。
朱永新:教育立法对落实依法治教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多次呼吁要加强教育立法。尽管我们已经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我一直认为教育立法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作为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也远远没有完成,目前我国很多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教育立法仅仅靠“六修五立”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国家的教育法治,需要上百部法律。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一直建议对整个教育立法做一个系统的规划,教育的所有问题都要纳入法律管理。
记者: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重要法律。但是,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还是时常觉得无法可依,对于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不知道依据何种法律来解决。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朱永新:一方面,我国的很多教育法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像《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很多条款已经远远跟不上现在时代的发展了。很多问题用现在的法律是无法规范也无法解释的。
另一方面,很多教育问题还没有立法,比如,我们没有《学校法》,校园里很多问题的处理没有依据。我经常举例说,一个孩子有先天心脏病,在学校突然去世了。这种情况根据国外的惯例,学校是可以免责的,但在我国就不行,学校就非得赔偿,而且家长大都要到学校闹事。现在,很多学校把单双杠都撤了,就是因为校长怕学生锻炼出事,一旦出事学校就得赔偿。比如,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学校图书馆等目前也没有相关法律,国外的《公共图书馆法》里面是含学校图书馆的,或者是专门设置有学校图书馆的馆法。
再比如,我们没有《考试法》,对考题泄露、招生徇私舞弊,只能按照经济犯罪的行贿受贿来处理。不仅是国家级的考试,学校的考试都应该有法律可依。政府的文件是不能替代法律的,法律在很多具体的教育问题上都应该有精细的规定。
如何理解基层教育工作者觉得无法可依这种情况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的法治意识不强,有法不用、违法不究。前年在贵州发生的四五个小孩子爬进垃圾箱窒息而死的事,后来查出这些孩子根本没有读书。如果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这是可以判的,父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明显要负监管责任,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如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的几部教育法,至今极少有过判例。我们有没有按照《教师法》处理过一起教育问题?有法不依,说明我们的法治意识不强。
二是很多法律条款模糊不清,无法执行。把法律写成了政府文件的形式,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就打折扣了。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立法先行,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相对来说,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里,教育这一块是比较薄弱的。
吴恒:目前,我国已经施行的教育法律有7部,按时间顺序来讲,《教师法》是1993年通过、1994年正式施行的,《教育法》是1995年通过施行的,《职业教育法》是1996年通过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是1998年通过、1999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是2002年通过、2003年施行的,《学位条例》(修订)是2004年通过施行的,《义务教育法》(修订)是2006年通过施行的。
有人把教育分成30个维度,比如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按照这30个维度,7部法律还不到四分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维度也在发展。不妨从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文案来切入,从2008年到2014年的7年间,新增加的教育维度多达12个,比如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等等。从国际教育发展态势来看,也有很多新的维度,比如慕课。教育的形式不同必然会带来内容的不同。现行7部教育法律不足以覆盖教育的需求,教育立法任重而道远。
对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法律困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很多人只看到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律分六大部类,教育是归到行政部类的。作为行政部类,就跟政府、公益性有密切关系。如果把刑法部类和行政部类的法律拿来比较,确实刑法的强制功能尤为显著,行政部类相对来讲强制功能不那么显著。很多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法律没有强制性,所以才会感到“无法可依”。举个例子,《职业教育法》对县级政府就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如第17条、第18条。然而,对这两条如果违反了,应怎么处罚,法律里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人感觉“无法可依”。
第二,对法律的执行力理解不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立法、执行、司法、相关保障,是一个整体,只有四个方面都做到了,才能称之为完备的法治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宪法、法律、国务院的条例、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构成的,并不仅仅限于法律和宪法,这一点必须要明确。
以民办教育为例,基层反映比较多的是举办者收取学费后卷款而逃,以及收学费的水平和办学条件的改善不相适应,教师待遇低等。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层面上是我们对法律执行不严的结果。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比如民办教育是民办非企业,在教育部门审批,在民政部门登记,是要年检的,实行财务报告制度。这些内容在《民办教育法》、国务院相关条例以及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出台的行业规章中都有相关规定,如果严格按照这些办法来依法年检,我相信这些违法行为基本上是没有空间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重审批、轻管理,执法不力。有法不依或不严格执法,法律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