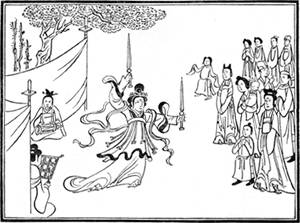马克·吐温的历史命运
马克·吐温可惜的是,布鲁克斯在选择马克·吐温作靶子的时候,由于对西部文化的无知,又套用他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知识,使自己丧失应有的说服力。
布鲁克斯的观点自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批驳最猛烈的是伯纳特·德沃托(Bernard Devoto),他的《马克·吐温的美国》(Mark Twain’sAmerica,一九三二)是捍卫马克·吐温的代表性著作。
德沃托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西部文化造就了马克·吐温,而不是相反。二、马克·吐温到了东部以后,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绅士阶级。
德沃托本人来自西部,是研究西部文化的专家。他认为,西部并非一片沙漠,黑人、印第安人和来自各地的白人拓荒者、移民,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在拓荒活动中形成不同于东部的西部文化。许多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经过说故事人、记者和作家们不断的艺术加工,具有粗犷开放、幽默、诙谐等特色。马克·吐温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加以发展创造,成为杰出的西部作家。他作品中宽广的视野、诗的质地也都与拓荒地区的大森林、大河和大草原密不可分。德沃托指出,西部也有坏的方面,凶杀、赌博、宿怨、格斗等等时有发生,这一些也在马克·吐温作品中出现,所以马克·吐温表现的是大西南地区整个的文明,是美国的全面形象。
《马克·吐温的美国》还认为马克·吐温夫人和豪威尔斯为马克·吐温作品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删去粗话、俗语和有可能得罪人的用语,不仅不涉及主要内容,反倒帮助马克·吐温去掉西部幽默中一些低级的东西。“改造马克·吐温”既谈不上,又何来“出卖自己的天才”呢?德沃托总的结论是:
在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接触到美国生活这么多的方面。他思路阔广,不安于现状,不知疲倦,什么事情都要探个究竟。有人说他的幽默不触及那个时代的弊端,实际情况是: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发现他那个时代的弊端很少不被他嘲弄过、讽刺过、讥笑过。政府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包括贿赂、腐败、收买、把人民的正义当儿戏等等,他全评论过。有人说他向社会上的庞然大物投降,然而抨击那个腐败的美国的批评用语“镀金时代”,正是他想出来的。在他创作的宽阔范围之内,社会的烂疮疤他没有一个不揭的。⑤
《马克·吐温的美国》出版后,马克·吐温的批评家们明显分成两派。德沃托之所以没有完全说服布鲁克斯派,原因在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德沃托或者没有涉及(如马克·吐温作品艺术质量的不平衡问题),或者轻描淡写(如后期悲观情绪问题)。这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依然关系到对马克·吐温的总评价。马克·吐温许多材料尚未问世,也使两派分歧无法终止。正如德沃托所说“在这些材料未公布的情况下,对马克·吐温的一切批评都不是定论。”
布鲁克斯与德沃托两派之争,也反映到三十年代美国左翼文艺批评家中来。V.F.卡尔弗顿在《美国文学的解放》(一九三二)一书中批驳布鲁克斯的“失败说”,认为马克·吐温《傻子国外旅行记》(一八六九)是“头一部美国作品”,因为“其中的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艺术方面”。照卡尔弗顿分析,“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全美国甚至美国的劳工运动都是受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所控制,他所能采取的最先进的立场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吐温这样的人来说,这通常就是革命的立场。”同样是左翼批评家,《新群众》的主编G.希克斯却同意布鲁克斯的观点,说马克·吐温如果“不屈从于传统的压力”,“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小说家”,而现在只“落得个供人消遣的作者”。埃德加·李·麦斯特斯要求更严,批评马克·吐温只把阶级斗争当作背景,没有当作题材来描写。
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在下面四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趋于一致的。
第一,马克·吐温是富于美国民族特色的作家。大家几乎都同意V.L.派灵顿教授⑥的意见:“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在美国土生土长,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在他身上,欧洲的东西一点都看不见,封建文化最后一条碎片都不剩了。他是地方的、西部的、又是美国大陆的作家。”
第二,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美国名著,无论从社会内容、思想意义,还是从艺术风格、语言技巧方面考虑,都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永远散发出“非常清新”的“青春气息”。⑦
第三,马克·吐温是雅俗共赏的典范。他的作品,读者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文化修养高低,都喜欢读。这是因为他一些优秀作品具有众多的层次,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幽默形式表现出来。他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既沟通了他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渠道,又以丰富的艺术含量进入严肃文学的领域。
(四)马克·吐温的语言艺术是卓越的。他只读过小学,他的语言是从群众中学来的活的语言。他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加工锤炼,进一步创造了美国的文学语言,开了一代文风。
四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摆脱了两派之争,对马克·吐温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成果是出现了几部优秀的评传和《神秘的陌生人》真本的发现。⑧
如果我们可以把批评家比作画家的话,那么,马克·吐温已经有了好几幅画像。第一幅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是一名滑稽演员,诙谐幽默,插科打浑,妙语不绝,逗得观众捧腹大笑。在他去世前夕,他的肖像变了:一身白色服装,一头银发,叼着烟斗,斜靠在椅子上,庄重而又慈祥,是一个大文豪在繁重的创作之余偷得一点悠闲。这幅画挂了二十年,布鲁克斯炮制了第三幅:一个唯唯诺诺、卑贱得神经虚弱的庸人,天才的英气好像隐约可见,但湮没在商业化的浓艳俗色之中。德沃托很不满意这种画法,来了个第四幅:才气横溢,粗犷豪放的西部性格呼之欲出。至今为止,马克·吐温的画像没有“定稿”,美国的批评家—画家们正在勾勒各自心目中的马克·吐温。
正当美国学者进行多方面构思的时候,苏联学者们给马克·吐温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像形成于五十年代以前,是一位高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大旗的战士。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画派的画法。五十年代末,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由苏联《文学报》一篇署名扬·皮瑞兹涅茨基的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批评美国学者查尔斯·奈德编写的《马克·吐温自传》(一九五八),认为“美国官方企图忘掉这位伟大的作家”,不得已时只好“抹掉马克·吐温讽刺中灼人的愤怒色彩”,把他说成一个“心肠慈悲、头脑简单的嘲弄家”,“新版的《自传》正是这种‘文学美容’的必然产物”。⑨
奈德就皮瑞茨涅斯基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他认为分歧在于对马克·吐温的基本看法。他认为“马克·吐温当然首先是一个幽默作家”,“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政论家”;可是苏联人却认为“马克·吐温首要意义在社会和政治评论,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美国社会。”奈德说,这种说法,“在多数美国人看来觉得奇怪”。马克·吐温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是“热爱美国的”。
这场争论典型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向和方法。应该承认,美国学者多少存在忽视马克·吐温政治性材料的倾向。例如,奈德把马克·吐温的小品、杂文、政论视为“沉闷的新闻文字”,又如,关于《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的论著浩如烟海,但很少有人去钻研他的《镀金时代》(一八七三)和《赤道环游记》(一八九七)。关于他后期的悲观哲学,美国学者常常孤立地探讨他的心理因素,却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同他晚年激烈的政论联系起来作横向的综合研究。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但苏联的批评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文学批评即社会批评的思想指导下,过于强调马克·吐温直接抨击社会和政局的作品,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进行审美的考察。由于二次大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突出一下马克·吐温揭露“金元帝国”的作品和反帝政论是完全必要的,这正是文艺批评多功能的表现。但第一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创作家,第二对他非文学的作品也要持客观态度。例如,马克·吐温在嘲弄欧洲君主政体的同时情不自禁地赞赏美国共和政体;对于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他也积极地提过改进意见,还身体力行参加过竞选活动。承认他有赞扬美国民主一面,不等于贬低他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不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呢?如果把马克·吐温与“镀金时代”隔离开来,把他孤立化、绝对化,那就把他当作神而不是人了。至于只向读者强调于论者有利的一面,瞒下不利的一面,这恐怕与马克思主义相去更远。
我国早在马克·吐温生前就有了他作品的译文。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凡属重要的,几乎已经都与中国读者见了面。在研究评论方面,我们解放前后分别受美国和苏联学者观点的影响。解放前,我国对马克·吐温的评介多数采取约翰·梅西(John Macy)的观点。梅西是美国文学史家,他充分肯定马克·吐温的成就,又批驳过布鲁克斯的观点。解放前介绍过马克·吐温的曾虚白、赵家壁都参照了他的观点。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推荐过布鲁克斯的《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但估计未必研读过,至少没有受它的影响,因为茅盾主要赞扬马克·吐温的民主思想。鲁迅《夏娃日记》小引中说,“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后来“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这些话听来有布鲁克斯的味道。不知是鲁迅看过有关论著,还是出于艺术的直觉?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