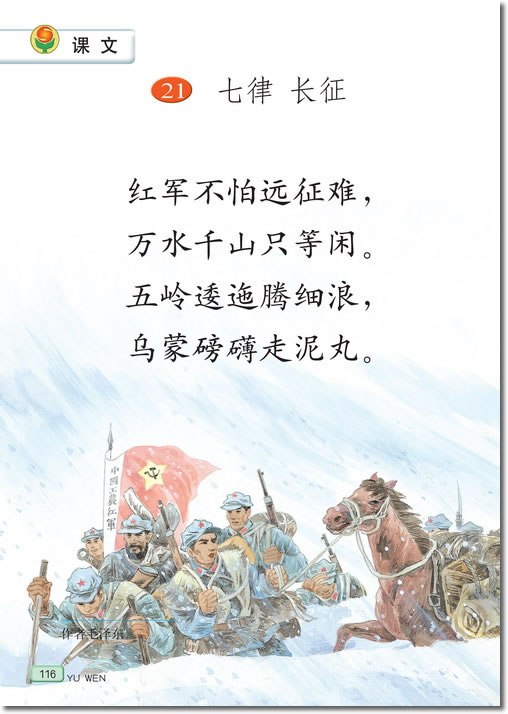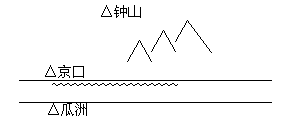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再起波澜
鄂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清明上河图》20世纪50年代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73年揭裱此画时,在画首约80厘米处删除了一块。当时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称:“卷首稍后,在汴梁市郊店铺林立的街衢上,一队扫墓后匆匆返回的轿骑,其前导的一马(其实不是马,而是公驴——王开儒)突然发情狂奔,在此惊险关头,一老翁赶忙抽身欲抱蹒跚学步的幼孙。原在老翁背后柱之旁残缺一大片,原绢已失,到明末清初揭裱时补绢画了一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故1973年新裱时揭下,留存归档,不再复原。”
我在农村长大,老实说吧,当时看着故宫领导从国库里提出来的《清明上河图》原件,激动得手脚也凉。
但是我骨子里毕竟是农民出身,伺候过各种牲畜,对农村的牲畜实在是太熟了!拿过画,就潜意识地先注意牲畜,哎,你可别笑话,庄稼人可在乎牲畜了!
这是本能。我首先转过的念头是,这张择端是不是也是老农出身,甚至像贩牲口的,笔下的牲畜竟然没有一个错位的!他画的马,都肢体粗大,耳小尾粗,鬃长下垂。他画的骡子体壮似马,但耳朵一定比马大,尾巴细,鬃毛直立不垂。他画的驴则体小耳大,头长腿细,尾细,立鬃且短,叫时嘴大张(只有驴嘶叫时候嘴巴大张,这是它们的特性),我怎么找茬也找不到。
但在卷首,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并且暗暗吃惊,那就是因为对农村生活不熟,对牲畜知识一无所知,故宫的专家们在解读各种牲畜时陷入一片混乱!
或指骡为马,或指马为驴,或指驴为牛,他们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牲口,就此误判了一段精彩情节(见前文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所述),他所说“尖嘴立牛”其实是艺术大师精心刻画的一头发情的壮年母驴。尽管年代久远,绢素残破,但发情母驴之神态毕肖,即便是接笔也是有据的。再看拴在斜对面铺下张嘴嘶叫,四蹄翻刨的牲畜,体小,耳大、立鬃不垂,正是一头公驴。
从各种角度看,这个画面正是一场驴们的精彩绝伦的“三角恋爱”——
在嫩柳初绿的道上,一富户十数人扫墓归来,男主人骑马,女主人坐轿,轿顶上插有杨柳枝条(点明了清明节)。这一行人在街口与也是扫墓归来的夫妻俩相遇。那丈夫头缠柳枝,赶驴在后。披斗篷的妻子骑公驴在前(已模糊),偏巧正与路边老者牵的那头发情母驴相遇(清明前后正值驴发情盛期)。那公驴狂奔扑向母驴,把主人掀翻在地,而那母驴即张大嘴嘶叫(发情母驴的特性),耳失常态,腰向上弓,尾巴稍夹,拼命挣向那公驴。牵母驴的老者吓坏了,一手狠拽缰绳,另一手忙招母驴前的小孩赶快躲避。那赶公驴的男人见妻子危险,惊慌地赶过来,旁人也呐喊救援。拴在斜对面铺前的公驴,也钟情母驴,四蹄翻刨,张嘴嘶叫,铺人无不侧顾。而对面的两头牛却无动于衷。
然而,由于故宫专家疏于农村生活,把公驴误判为马,把母驴曲解为尖嘴立牛,并认为殊碍画意,把巨匠的生花妙笔删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残画。后人读画,就此读不懂这一大段画意。
因为在他们的解读下,马,无端地发情;牛(尖嘴)无端地狂叫,画意就无人能懂了。
我记得我当时犹豫了很久,终于战战兢兢地对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说,此处原是发情母驴的位置,好像不该删的。
杨院长当时说,此处是搭凉棚的树杈子,不是驴头,明清人接错了。
我没敢再争,怕他们不要我复制了,可是心里存了一个铁疙瘩:这幅神品的卷首就这么永远让人读不懂吗?我发现了沉冤而不说,怎么对得起子孙后代?
“你怎么如此有把握解释这个千年之谜?”记者至此忍不住要发问,“你毕竟不在母驴的发情现场”。
嗨,我亲身领教过发情公驴的厉害!他说着一拍手叙述了一段40年前的往事,那年春天搞“四清运动”,我和同伴骑着两头公驴下乡,走着走着那俩公驴浑身发硬了,打摆子打喷嚏流涎水就是不走,我们一看,30米外的槐树上拴着的一头母驴这时正张大着嘴喊叫,驴叫驴叫,那个声音之响可以震聋你的耳朵!突然,我们的坐骑像是约好似地狂奔狂跳起来,把我们俩都颠倒在农田里,发疯一样地朝母驴狂奔,那真是排山倒海的激情,顺者昌,逆者亡。你见识过一次就永远难忘。
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一见《清明上河图》的这个场面,就唤起了记忆。生活的确是创作之源,白居易念诗给老妪听,就是因为老妪懂生活,不怕你们笑话,你们不妨把这段画面修清楚了,放大了给我们农村的老农看看,保管能懂!比专家强多了!
“但是,故宫毕竟对你不薄,你这么做心有不安吗?或者,你和故宫有什么不便说的过节?”
没有。没有什么过节。他说,故宫对我确有“恩典”,但是对民族、对子孙来说,这“恩典”就小了。我复制《清明上河图》成功以后,无数次向他们提出,要他们纠正,他们就是不理,我只能向舆论公布。
“那你现在和故宫的‘协议’怎么样了?”
“那,当然是吹了。”
他面色沉重地把我们送出了秋风萧瑟而劫后重生的唐山大地。
(此文承肖关鸿、谢春彦、戴敦邦诸先生支持,谨表谢忱。)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
零零教育社区:论坛热帖子
| [高考] 20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大作业答案 (2022-04-25) |
| [家长教育] 孩子为什么会和父母感情疏离? (2019-07-14) |
| [教师分享] 给远方姐姐的一封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伸缩门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回家乡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是风味也是人间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一句格言的启示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无规矩不成方圆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第十届全国教育名家论坛有感(二) (2018-11-07) |
| [教师分享] 贪玩的小狗 (2018-11-07) |